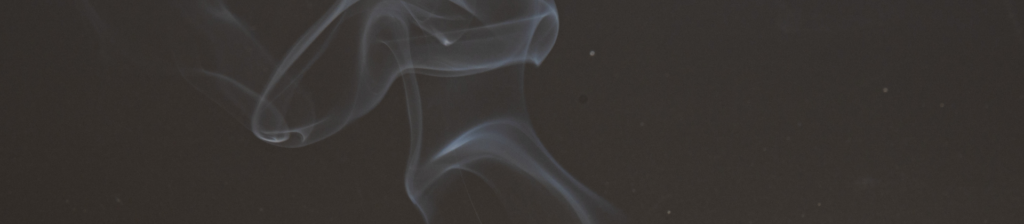
普鲁斯特全集》1
寻找逝去的时光》第一卷:走向斯旺家族
原文:普鲁斯特 翻译:井上久一郎 1984年第一版,筑摩书房
第56-61页:对普鲁斯特效应的部分描述
我觉得凯尔特人的信仰很有道理,根据这种信仰,我们失去的人的灵魂被困在更低级的东西里,一只野兽、一株植物或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当我们经过那棵树或得到囚禁这种灵魂的物体的那一天,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失去的人的灵魂,这对很多人来说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对我们来说,他们是失去的,直到我们遇到这样的一天,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永远不会到来。
但当这样的一天到来时,逝者的灵魂会颤抖着呼唤我们,一旦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咒语就会被解除。 被我们解放的灵魂,已经死去的人,会再次回来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的过去也是如此。 唤起过去是一种空洞的努力,我们所有理性和知识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过去隐藏在某种意想不到的物质中(以及这种物质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中),在理性和知识的领域之外,超出了它的能力。 我们是否在死前遇到这种物质,取决于机会。
从我的睡觉时间、我的戏剧,到ComPlay中对我来说没有其他东西存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在一个冬日,当我回家时,我母亲看到我很冷,与我平时的习惯相反,要我喝杯茶。 起初我拒绝了。 起初我拒绝了。
然后,出于某种原因,我重新考虑了一下。 她去买了一块糕点,是那种叫做卡奇特玛德琳的小而圆的松软的糕点,看起来就像被塑造成一个贝壳,有扇贝壳的窄脊。 不久之后,我被这沉闷的一天和另一个阴沉的前景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机械地把一勺茶水送到嘴边,茶水中我轻轻地溶解了一块玛德琳饼。
但是,当这口混有糕点碎片的茶水接触到我的味蕾时,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意识到我体内正在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一种奇妙的快感笼罩着我,一种孤立的、无法解释的快感。 它立即使我感到生命的转折无关紧要,生命的灾难无伤大雅,生命的短暂是一种幻觉,就像爱情的运作一样,并使我充满了某种珍贵的本质,或者说,这种本质不在我身上,而是在我本身。 是这样的。
我已经不再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或凡人。 这种强大的快乐究竟从何而来?我觉得它与茶和糖果的味道有关,但又无限地超越了这些味道,因此不可能是同一性质的。 这种快乐从何而来?它是什么意思?我到哪里去弄清楚呢?
我喝了第二口,在其中我没有发现比第一口更多的东西,第三口只给我带来了比第二口略少的东西。 我现在应该停下来了。这杯酒的效力似乎在减弱。 显然,我寻求的真理不在酒里,而是在我身上。 这杯酒唤醒了我心中的真理,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真理,我只能漫无边际地重复同样的证词,逐渐失去力量。 我希望我能重新找到它的原貌,现在就把证词保留下来,以便有一天它能对明确的澄清有所帮助。
我放下茶杯,反思自己的精神。寻找真理是精神的任务–超越自身能力的冒险精神。 但怎么做呢?我感到严重的焦虑,当精神,也就是探究者本身,成为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不得不在其中搜索时,当手头所有的知识完全没有用时,我感到严重的焦虑。 探索?不仅如此,它还创造了。精神面对的是还不存在的东西,只有精神能使它成为现实,并最终让它进入自己的光芒。
然后我又开始问自己,那个未知的状态是什么,它没有带来任何逻辑上的证明,但它带来的幸福的明显性,它的真实性的明显性,湮没了所有其他状态。 我试图让这样一种状态再次出现。 我顺着思维流回到我喝下第一勺茶的那一刻。 我再次发现同样的状态,但没有新的光。 我要求我的精神再做一次努力,把逃跑的感觉再一次带回来。
而为了让我的精神能够甩掉它试图在感觉中再次飞跃的每一个障碍,甩掉每一个与飞跃无关的想法,在面对任何飞跃时都不动摇,我捂住耳朵,不分散我对隔壁房间里的噪音的注意力。 然而,我感觉到精神已经筋疲力尽,做得不好,所以我强迫它做相反的事情:采取那种被禁止的休息,转移它的思想,在面对最后的考验时恢复精力。 然后我又在精神面前留出一片空白,再一次让它面对那第一口仍然新鲜的味道,我感觉到我体内有什么东西在颤抖,有什么东西想从下沉的地方往上走,有什么东西想从最深处被拉上来,像一个锚。 它是一种想要像锚一样被拉上来的东西,在很深的地方。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慢慢地上来了,我感觉到它的阻力,我听到它穿过的距离发出的沉闷的破裂声。
我看到什么东西在我的底部这样抽动,它一定是视觉上的回忆,一个与那味道有关的形象,并试图跟随它上到我的表面,但它的移动太远了,而且是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方式,它被激起了…… 黯淡的反射,混合着难以捉摸的不同颜色的漩涡,对我来说,多少是可以辨认的,但它的形式却不是,就像那个味道的见证,唯一可能的解释者,我不能把它的同伴–那个味道–的见证翻译给那个反射,它与它一起诞生,与它密不可分。 -我不能要求你翻译 “味道 “的证言,也不能要求你告诉我它与什么特殊情况、什么过去的时间段有关。
这个回忆,这个过去的旧时刻,会不会到达我清晰意识的表面,在这个时刻,一个与旧时刻相同的吸引力,从那么远的地方行动,现在在我内心深处,正试图催促、启发和激励这个旧时刻?我不知道。 我不再有任何感觉,回忆似乎已经停止,又重新沉入海底,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从黑夜中再次升起?十次,我不得不重新开始,向回想弯腰。 而每一次,那种让我们一提到任何困难的任务、任何严肃的工作就扭扭捏捏的胆怯,都劝我把它扔掉,只想着今天的疲惫和明天的欲望,我不痛不痒地反刍着这些,然后照例喝杯茶。
突然,一个回忆出现在我面前。 那是一小块玛德琳蛋糕的味道。在康普雷的星期天早上(因为星期天我在弥撒时间才出去),当我去莱奥尼姨妈的房间里说早安时,她会把她经常喝的茶叶,或者沼泽树花的浸液倒进去,我也会尝尝。 她会把马德琳饼浸在她经常喝的茶叶或木兰树花的汁液中,然后把它们拿给我。
只要我只看不尝,小玛德琳蛋糕就不会让我想起什么,可能是因为我后来经常在糕点店的货架上看到它们,但从未尝过它们,所以它们的形象在康布雷的那一天留给了其他更近的日子。 也许是因为它的形象离开了康布雷的那些日子,去了其他更新的日子,也许是因为那些久违了的各种回忆没有任何东西幸存下来,一切都被拆散了,这些物品的形式已经富于敬畏和虔诚的褶皱,糖果也充满了肉感,所以它们已经消失在过去。 糖果的小贝壳的形式,在其虔诚的褶皱中是如此的饱满和充实,也同样消失了,或者沉睡了,失去了使它们恢复知觉的膨胀力量。
但是,从古老的过去来看,在人死了,东西垮了之后,当没有什么可以存活的时候,只有一种味道,一种微弱但更持久的、更无形的、更坚持的、更忠实的、像灵魂一样的味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其他一切的废墟之上,保持着被记住、等待、希望、希望、希望。 它沉思,它等待,它希望,它在几乎无法察觉的单纯的气味和味道的斑点之上毫不退缩地坚持着,这是一个巨大的回忆的建筑。
当我意识到我尝到了我姨妈用含苞待放的花朵为我准备的一块玛德琳蛋糕时(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回忆让我如此高兴,我必须等到很久以后才能发现原因),我立即意识到我是在一个面向主要街道的房间,我姨妈的房间就在那里。 灰色的老房子里有我姨妈的房间,面向主街,看起来就像一个戏剧的舞台布景,在它后面,面向花园,通向为我父母建造的一个小附楼(我一直只能想象这个附楼的切面),和这个主楼一起,小镇从早到晚都在。 这个小镇在任何天气下都是如此,我经常在午餐前被送去的广场,我去办事的街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都去的小路。
就像在日本人的消遣中,把一张小纸片放进装满水的瓷碗里,这张纸在那之前一直不清楚,被拉伸、卷曲、上色、裂开,变成了坚实无误的花、房子和人,现在也是如此,在我们的花园里,日本人的花园,。 同样,现在,我们花园里的所有花,斯旺先生花园里的所有花,还有维沃内河上的睡莲,以及村里的好人和他们简陋的住所,还有教堂,还有整个康普雷伊和它的邻居,所有这些有形有实的东西,无论是城镇还是花园,都从我的茶杯里出来了。 城镇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里出来了。
